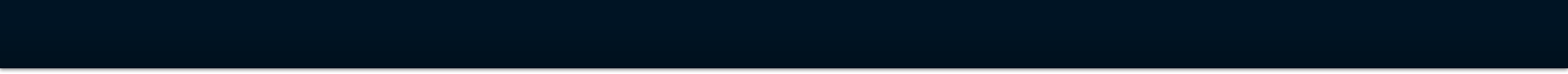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巴山轮会议
【编者按】今年是“巴山轮会议”召开三十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将于2015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举办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宏观经济研讨会。关于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已有众多与会专家、学者通过著述进行回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军所著《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书对1985年巴山轮会议进行了论述。现将有关书稿节选如下。
在中国,一提到“巴山蜀水”,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三峡。三峡两岸崇山峻岭,悬崖绝壁,风光奇绝。
在24年前,即1985年9月2日,它该是我刚刚开始硕士研究生第一堂课的时候,在这段属于长江三峡的江面上,有一条游船,它缓慢地从重庆驶向武汉。而在这艘当时属于交通部的长江游轮“巴山”号上,正在举行着一个由三十余位海内外经济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简称为“巴山轮会议”。
会议结束后共整理出了七个重要的专题。但实际上,船上的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应该怎样调控正在经历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在24年前,我们的政府和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对转型中的宏观经济及其治理的知识都准备不足。这些问题在“巴山”号轮船上讨论了整整一周时间,于9月7日在武汉正式结束。
24年后的今天,如果你在Google上搜索“巴山轮会议”,至少有25 800条关于它的信息,而且大多数是2005年“巴山轮会议”召开二十周年的时候,一些当时参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对它的纪念、回忆以及后人对它的评价。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是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非常活跃,不仅学者们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策略的研究,而且政府积极推动与支持,是双方互动最好的一段时间。
回首往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场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都津津乐道。而且,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那么“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这两次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我们先说到底都是哪些人参加了此次“巴山轮会议”。我的手头从1990年开始就一直保留着一本书,书名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事实上这本书可能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但又仅限“内部发行”的唯一一本关于“巴山轮会议”的详细资料。这本资料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这在之后,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辑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这是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文集。
这份资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它收入了“巴山轮会议”上讨论并由中国经济学家整理出来的7个专题报告和13位中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在书的封2上还插有一帧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与会11位国外经济学家的彩色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不少经济学家,尽管我只与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后来有过见面的机会。从照片上看出,中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高尚全、刘国光等参加了会见。而受到领导接见的国外的经济学家当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认出美国耶鲁大学的托宾(James Tobin)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教授、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任主任林重庚(Edwin Lim)博士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伍德(Adrian Wood)教授。
我并没有见过托宾教授本人,只是见过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于2002年离世。当年他在“巴山轮会议”上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而科尔内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声甚旺,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Shortage)是20世纪80年代极少数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此高超的分析能力的经济学著作,它甚至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范式。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短缺经济学》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在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中被广泛复印和阅读了。随后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而我与科尔内教授则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9月,在中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他应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邀请来中国参加其著作《短缺经济学》纪念译本1 000本的出版发行活动。那年他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在复旦大学,我邀请科尔内夫妇吃过饭。还有几次是在哈佛大学,在2000~2001年期间,我曾去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当面请教他,讨论转型的理论问题。科尔内教授后来还曾委托他的研究助理给我送来了多篇他的最新论文。
而我与英国经济学家伍德教授相识的时间则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期间,我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继续我的博士后项目的研究,当时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萨塞克斯大学内的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工作。我和他经常一起在IDS的餐厅吃午餐。那个时候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其实就是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的那本《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著作。这本书称得上是伍德教授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而在这之前,我是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项目报告上第一次看到伍德这个名字。他现在执教于牛津大学,2007年4月,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揭牌仪式上,我与他作为嘉宾巧合地被安排在第一场报告,同台演讲。
其他出席“巴山轮会议”的国外经济学家还包括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拜特(Aleksander Bajt,前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凯思克劳斯(AlexanderCairncross,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现已去世)、琼斯(Leroy Jones,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现已去世)、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小林实(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调查部主任,现已去世)。
有意思的是,出席“巴山轮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人员几乎都不在大学教书,多半是在政府和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或官员,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主办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的学院派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尽管“莫干山会议”上已经有不少青年经济学者崭露头角。
如果以当年出席会议者的年龄为序,那么,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81岁,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2005年7月病逝)、安志文(67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6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马洪(65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6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百岁老人薛暮桥先生,因为他的一本书对我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影响甚大。我在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读经济学时看的第一本涉及中国经济的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薛暮桥与邓小平同年出生,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宿将。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建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的经济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校”耗费11年心血、7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发行1 000万册,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启蒙教材。2005年3月,他与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4人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50~60岁年龄段的会议代表是戴园晨(59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58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56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5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55岁,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51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7月病逝)。
50岁以下的参会者包括了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45岁,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33岁,时任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31岁,时任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29岁,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编者注:青年代表还有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李振宁,他是科尔内所著《短缺经济学》的翻译者,与会的三位正式青年代表之一,现在是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内领先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者,本次纪念研讨会的积极倡导者和共同承办方。)
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资料写的序言中可以判断,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和设计的。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协助(林重庚博士是当时的办事处主任)。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上述参会学者,大概60岁以下的,还分别负责书面整理了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在“巴山轮会议”上,经济学家们重点讨论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从概念上厘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目标以及经济调控的手段等。会议最后形成了七大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
没有必要全面介绍这七个专题的讨论内容,需要重点回顾的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可能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在实际上产生了影响。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与战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再一次的长征。
关于过渡的方式,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揽子改革”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整理出来的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托宾的这番话曾被解释为“中国10年内不要搞资本市场”。而且这番话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辩论中,多次被吴敬琏教授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个意见对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应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对中央的决策可能产生了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以及如何实施宏观治理的政策。会议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需求,用托宾的话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作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何治理过度需求的问题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地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谓“双紧方针”),并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和中央银行的职能等技术性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改革建议。
此外,会议上还特别针对收入分配的政策进行了研讨,这是因为在当时,工资上涨和消费基金的膨胀蔓延正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尔内教授指出,经济改革有很多风险,主要风险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托宾的意见是,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
在开始改革之后,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资增长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局面迅速蔓延。在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大型调查中,获得了1984~1985年间工资上涨和消费膨胀的实际信息。根据这一调查报告,“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我们调查的城市消费基金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建国以来罕见的。1985年,三种消费基金还将比去年再增加800亿元。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基金的全面膨胀”。
该报告还调查了消费基金膨胀的特征。根据调查发现,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表现包括:(1)企事业单位超发奖金、滥发实物、随意增加津贴、扩大浮动升级;(2)“账外洒漏”:即单位通过“账外”方式发放和增加各种职工收入。如套取现金、公款私存、利用劳动服务公司作为小金库、对外承包等;(3)国家用于职工福利、物价住房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长。这就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成本(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了。在当时,账面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种福利支付和补贴,工资性支出比重则达到了15%以上,超过了日本 13%和前苏联15%的水平。
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转入更加隐蔽以及采用“体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国家统计局对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产生严重的向下的误差。调查报告中对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与来自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跃性地扩大了。
那么,怎么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呢?在“巴山轮会议”上,布鲁斯提出,单纯使用经济手段难以保障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确关系,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托宾也主张,中国政府不能马上放弃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议把目前由银行监督工资总额发放的办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时工资水平的办法。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使用的对超额发放的工资实行征税的政策应该严格执行。但是,总体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由于工会组织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资过快增长的经验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把工资与物价挂起钩来,这种“收入指数化”的主张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同。
从1985年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大大低估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以及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不过,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1985年组织的那场大型调查报告对中国如何解决工资增长过快与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却超前地作出了重要预测。这份由李峻和夏晓汛负责执笔的调查报告《消费膨胀: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结束部分这样写道:“在当前宏观失控局面未扭转之前,为了巩固现有的各个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机会,对消费基金加强行政管理约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就中长期来看,对劳动力价格的管理从僵硬的计划管制下解放出来,开放劳动力市场,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潜能释放出来,由市场机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相对工资水平,从机制上抑制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把国家从烦琐的具体工资标准的设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从事宏观分配政策和工资基金总量的管理,是改革的方向。”事实证明,今天倒是真的做到了。
来源: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军所著《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书,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